|
刘丹 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之中,人们对社会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的期待,认为它是“最接地气”的学科,是接近生活的,甚至希望认为它能为解决人和社会的问题提供方案。但其实社会学与社会也存在着距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的空间破土而出,不断成长,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议题。图为流动中的人们,来自王福春摄影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6月)。点击图片可打开已推送的文章《在今天,社会学与社会有多远的距离?》。 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以来有社会学家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进入社会的公共生活,在不同程度上拉近与社会的距离。(在学科内从事专业研究,也可基于“问题意识”拉近距离)致力于这一项事业的包括为人们所熟悉的孙立平、郑也夫、李银河、潘绥铭等社会学家。今天的青年社会学者也在不断以新的方式实践。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专访郑也夫、李钧鹏和严飞两代社会学家聊了聊他们理解的公共生活,以及参与其中的故事。 1950年出生于北京的郑也夫经历过“知青”岁月,恢复高考后考入首都师范学院,先后供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自1983年以来,郑也夫持续在媒体上发表时评和专栏文章,雄辩的文风成为了他的标志。他涉足过的公共议题包括推行“沙葬”文化、讨论水价和燃油税、为“野泳”辩护等。此外,郑也夫也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撰文著书。 当然,新一代社会学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更为多元化:做公开演讲,参加沙龙,翻译学术作品,从事通识写作,等等。严飞从2005年开始就在进行面向公众的媒体写作,去年出版了《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社会学通识读本,在读者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钧鹏很早就关注社会学者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话题,近年来同时主持着多项跨学科学术译丛的工作。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01 对话郑也夫: 辩论是一种公共生活 郑也夫,生于1950年,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荣休),著有《文明是副产品》《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等。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相比于其他学者,你可能是国内最乐于在公共场域发表评论和观点的学者之一。喜欢写文章对社会现象表达观点,吸引了很多专业领域之外的人士关注。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独特的道路的?
郑也夫:这是从我对社会的牢骚开始的,我把它叫做童子功。 我当“知青”的时候还不到18岁,做了8年半的“知青”,在性格的塑造期被赶到了农村,远离了课堂,不再读书。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看到社会中太多不合理的现象,由此就开始向周边人发牢骚。当然发牢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知青”,或者当地的成年人。但是在这当中应该说,我发得最多,也发得最精致,所以说出来的一些正理和歪理能赢得听众。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1977年上了大学,之后为了饭票的问题又考了研究生。但是,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我学的专业都不是社会学。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国家恢复了社会学,这让我眼前一亮。 我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发牢骚的对象是社会的不合理之处。我本是个看待社会问题的业余爱好者、一个牢骚满腹的青年,没想到我的爱好居然可以成为一个专业,可以发点专业的“牢骚”,还可以挣工资,我就乐此不疲地进入了社会学的大门。 于是我马上就开始自学,毕业论文选的也是社会学题目,毕业后我就毛遂自荐去社会学研究单位,正式走上了研究社会学的道路。可以说,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观察和评论,跟我在“知青”时期的性格与智力生活的追求接上轨了。 我平时会写两种文字,一种是写学术文章和著作,还有一种是写时评。最早一篇时评应该是1983年写的。那时中国学术评价很不公正,我的职称评定推得很迟,但我写的时评文章获得了不小的社会声誉,拿了稿酬,还获得了相当多的知名度,这就更让我一发不止了。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延续到了你的教学之上。比如你会给学生布置作业,调查身边的教育现象,在课堂教育上,社会学如何实现应有的关怀呢?
郑也夫:我不会在这一点上试图影响学生。但是,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做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对学生的培养,这是一个他们最应该具备的本领。我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反对从理论到理论。我在美国受了一年半的教育,原来是一个酷爱理论的人,没想到我所就读大学的社会学系,不允许学生写纯理论的、“从书本到书本”的硕士论文。硕士以下的学生,首先要做的是经验调研的学习。这跟我的认识完全合拍了,我也认为年轻学生多数人做不了纯理论的。 2004年一个叫布洛维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主张的概念和我一拍即合。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公共社会学家。我天性喜欢议论公共事务,看了他的演讲很受鼓舞,他帮我正名,这是很正义的事,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学科。所以我也在我的教学中推广,不要学生“抄书本”,写一篇没有任何创意的所谓理论文章。 《公共社会学》,[美]麦克·布洛维 著,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议论过的公共话题数不过来,有“轿车文明批判”、推行“沙葬”、学术评价的有限匿名制讨论、反对抽水马桶、讨论水价和燃油税、为“野泳”辩护、中国足球,还包括近些年你一直关注的教育问题。这么多看似“风马牛不想及”的话题,似乎从来没有难倒过你。这么多年以来,你有过犹豫吗?你担心过会遭到反对意见的攻击吗?
郑也夫: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生活的社会上一直有不合理的、需要反思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一路走下来了。涉猎这么多领域,在我看来也不是问题。社会现象的不同方面,可能隔得很远。我首先是个普通的公民,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会发牢骚。 我在社会上发的时评文章有几百篇之多,它们不是学术文章,不会接受来自专业方面的挑战。我认为,在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当中,我的文章是比较雄辩的,下的功夫也是比较扎实的。 另一方面来说,我从来都愿意接受挑战。我一直说,如果你要挑战我,你是看得起我,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个问题以更大的强度来推向社会。一个人的独角戏可能不足以让社会关注。对于辩论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畏惧,我也并不担心我的东西有漏洞,谁的东西一点漏洞没有。比如说,关于轿车问题,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文章之后,樊纲就回应了一篇,我再回应,再反驳。 后来我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关于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也引起了社会比较大的关注,总共大概有六七篇文章批评我的这篇文章。我也回复了一篇。我非常高兴迎接这样的论战,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没有人愿意和我进行论战。很多时候我向别人开战,别人不回击,我自己写的东西遭到过几次攻击,我回应之后,又没了声响。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和你辩论下去?你觉得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
郑也夫:中国社会中的论战从来就少,我的一个猜想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媒体的智识生活,似乎就不习惯于古希腊哲学家那种类型的论辩,很多学者和公民不擅于在公共平台上摆出价值和立场,怕得罪人。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异类的,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也许这个问题你得问他们,因为我不怎么畏惧,就不太清楚畏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过的一些看法,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立场,推翻原先的说法吗?
郑也夫:我大概只记得一个。可能是我最早自己察觉了,马上认识到了当时的想法错误,就更改了观点。当时讨论的是高校录取的比例,讨论有多少考生做分母,有多少人录取做分子,总之录取率非常低,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生压力很大,于是社会上就产生了很多函授大学、工人夜大等学校。 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说这样的学校不要办,办教育还是要正规一点,正规高校教育可以扩招。但我自己记得,这句话说过没多久,国家真的开始了扩招政策。我马上就醒悟了,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中国需要更多的是好的技工。在“反扩招”这件事情上,我的观点有些反复,但总体来说是非常稀少的。而关于职业教育,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专门谈这个问题。 《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3年9月。 新京报:因为发表时评,你早年也受邀当过北京交通顾问,策划并主持过电视台的节目。你怎么看待学者发表的时评文章对社会的影响?
郑也夫: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在言论的层面,我的观点应该说大获全胜。比如说我反对发展私车的问题,在言论的层面上没有敌手。再比如,我曾在《新京报》发了很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希望北京的一些公园(比如玉渊潭公园)能保留野泳者游泳的场地,没有人能争论过我。但是,在社会实践层面没有改变结果。不过作为一个言论者,我至少可以努力影响让社会的言论空间呈现多元化。这可能就是我能做到的效果了。 02 对话严飞: 公共写作对专业也有促进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等通识著作。 新京报:从你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介入公共生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近年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做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
严飞: 社会学家怎样介入社会中的公共生活,我认为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利用我们的专业研究和田野实践,通过社会学干预实验增进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第二个维度,则是通过知识的分享和扩散介入公共生活,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通过普及人文通识和社会学的教育,让大家认识到原来社会学的现象和原理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发生,让更多人关注和倾听我们社会里的多元声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做的“新清河实验”是利用社会学家的力量,在社区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这是社会学干预实验的典型案例。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等人连同社会学系的学生就在北京海淀区的清河做过一次“清河实验”。抗战爆发之后,老“清河实验”被迫中断。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老师主持的课题组与海淀区政府合作,重启了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也就是“新清河实验”。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李强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新清河实验”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升当地社区的融合度和社区团结。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因为清河的人口构成复杂,当地社区的参与度与社区的认同感非常低,邻里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李强老师带着学生进入社区,通过空间的改造,积极地促成来自不同社群的居民一起来有机地建设清河社区。比如说,促成建立居民议事堂,就社区里的公共事务一起讨论;建立亲子的活动空间,通过亲子阅读把不同群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发动居民共同植树,做社区公益,等等。 在我看来,李强老师带队的“新清河实验”就是社会学干预和介入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案例,用专业的社会学调研进行干预实验,是社会学介入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新京报:高校教师首先注重科研和教学,而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工作常被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一直很乐于参加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和沙龙,去年出版的社会学通识读本《穿透》也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好评。从事通识写作的初衷是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从事这项工作的经历和感受?
严飞: 我在进入学术圈,正式成为大学老师之前,经常从事媒体写作,为我现在面向公众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我以独立学者的视角在媒体上写过大量的文化评论和书评。现在回过头去反思,我觉得当时所写的媒体文章缺少两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缺少历史的纵深感。社会是层累的,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运作的逻辑,在今天依旧有一定的适用性。现在我在面向公众写作的时候,更愿意带领读者用历史的想象力来理解今天社会的变迁。第二,我也更注重把经验材料作为论据来使用,加入更多案例、故事、统计数据、生命史的记录,来更好地向公众表达社会学的理念。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 我特别喜欢面向公众的写作,我觉得这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有促进。诚实地说,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不算在工作考核指标当中,这意味着你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的时间投入在不计入工作成效的事情当中。但面向公众的写作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帮助我用比较容易让公众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观点。社会科学很多时候会使用非常复杂的语言进行一种学科专业化的表达。面向公众的写作会不断地提醒我,最好的社会道理实际上是使用一种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语言把故事讲出来。只有看得懂,只有让更多的人读到,才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共鸣。 此外,面向公众的写作也能让我听到更多的读者反馈和批评。这让我意识到,很多书本上的西方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转型中会存在落差。真实的社会场景存在很多不同的面相,读者的反馈引申带来的鲜活故事和场景让我重新思索理论的缺失。前不久,我在一场活动上和日本岩波书店的前主编马场公彦先生进行对话,讨论东亚社会的社会发展和现状,特别是今天面对一个内卷化的时代,日本社会是怎么做的?这种对话实际上对我来有很大的启发。同时现场读者也会提出非常有趣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流行词“内卷”和“入关学”,如果说“内卷”是指个体层面上的,“入关学”是不是在国际层面上的一种“内卷”?这样的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目前正在写的一本书,关注的焦点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外来务工者。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不断地做基层的田野访谈。最后精选了其中8个有趣的小故事。这本书用生命史的方式呈现这些故事,再加上社会学的分析,我想让大家认识到,我们今天身处于经济高速迭代发展的时期,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普通人的声音同样值得记录,他们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是牺牲掉了自己,也牺牲掉了整个家庭,经济上、精神上都在面临失去、迷茫和挣扎。同时,他们对于未来也有期待,他们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03 对话李钧鹏: 介入公共议题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翻译作品有《为什么》《功与过》等。 新京报:有些人主张,社会学者应该是社会现象的冷静旁观者。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学者自己也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学者与社会的合适距离是怎么样的?
李钧鹏: 社会学内有一种“公共社会学”的主张,专门讨论社会学应该如何介入公共议题。我2003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正好赶上当时的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各大高校做关于公共社会学的巡回演讲,我当时也很激动。布洛维的口才非常好,在这次演讲之后很久,公共社会学一直是社会学系学生日常讨论的话题。在这之后几年,美国社会学界围绕公共社会学做过激烈的辩论,我当时比较密切地关注这个议题,后来也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谈公共社会学》,对这个话题做了一些思考。 社会学者介入公共议题的方式可以有多元化的渠道。有的学者乐于做访谈、上电视,我也很佩服沈原老师这样投身于卡车司机调查的社会研究。再比如说,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关心和提携后辈,在我看来也是社会学者介入和影响公共生活的维度。 我很关心我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困惑,我都愿意提供建议。我也使用“豆瓣”这样的社交平台,经常有包括外校的学生在“豆瓣”上联系我,让我推荐一些书,解答学习上的困惑,或者为他们报考研究生出谋划策,等等。我很乐意和这些学术后辈交流。这样的方式可能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这可能是中生代学人和新生代学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 另一方面,社会学者介入公共议题,也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现在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出现之后,媒体经常会找一些专家做访谈,或者上电视。但是,它有可能很容易就沦为一种非常廉价的媒体点评。每一个人,包括社会学者在内,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这里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社会学家也应该用专业知识的武器来反思自己的立场。 我经常会反思自己的立场,反过来说,我对自己的立场也不是特别有自信,我不觉得我的观点就一定比别人更具有科学性,所以不会有很强的意愿说服别人。在课堂上,我也以传授知识为主,尽量力图避免在不经意间给学生灌输所谓的人生道理。 由李钧鹏主编的“历史-社会科学译丛”,收录翻译作品《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美]菲利普·S. 戈尔斯基著,李钧鹏、李腾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2021年2月)。 新京报:其实你从事的学术翻译工作也是社会学者影响公众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能不能介绍你正在准备和打算出版的翻译计划?
李钧鹏: 学术翻译在社科院系中的认可度非常低,在我们这里完全不算学术成果。在做学术翻译的过程中,我也有过无数次打退堂鼓,想说我不再做了,但最后还是断断续续坚持在做这个工作。 网络上对此也有过很多争论,有些人说,我们翻译的书已经够多了。有些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能看懂英文了,没必要做学术翻译了,我对此都不太赞同。就我的观察而言,学术翻译还是很有价值的,我周围学生中的大部分人接触不到英文版原书。即使可以通过网络下载,由于语言的阅读能力有限,也没有老师指导,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从何谈起。如果你真的深入翻译的体系中,你会发现国内的翻译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块是我们的欠账,特别是比较好的译本。所以,我很希望把一些经典的、有价值的好书引进到国内。 我现在手头在做三套译丛,一套是和北师大出版社合作的“米尔斯合集”,《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之后,这个系列还会有其他的书待翻译。第二套是历史-社会科学译丛,今年刚出版了《规训革命》,第一辑计划出6本,打算在年内能出版第二本书。还有一套是和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分社合作的“剑与犁”译丛,收录的是一些和国家建设与社会冲突相关的书籍。 因为我的精力有限,而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基本上每一本书我自己都要过一遍,即使不是我翻译,也要提一些意见,所以几个译丛的翻译进展都不算特别快。 《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理由》,[美] 查尔斯·蒂利 著,李钧鹏 译,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9月。 新京报:你曾在访谈中提到过一个观点,你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场域和学术场域进行了完全的分离。这种时代环境的变化与我们讨论社会学者介入公共生活的话题也有密切的关系。你觉得一种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李钧鹏: 我觉得二者之间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良性互动,思想和学术不应该是完全脱节的两个场域。目前的现状是,在公共议题上面,我们的思想场域还不够活跃,至少还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思想场域还不够活跃,是因为我们的学术场域出了一些问题。理想的状态下,学术应该可以反哺思想,比如说,我们的选题应该可以百花齐放。社会学关注的议题没有绝对的“大”和“小”。有些学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完全不注重“阶级-国家”这样的分析工具。有些老一辈的学者更关注社会转型之类的宏观话题,但不鼓励甚至反对学生研究性别议题,这在我看来都是不好的做法。我是一个多元论者,无论是选题,还是就方法层面,我都主张百花齐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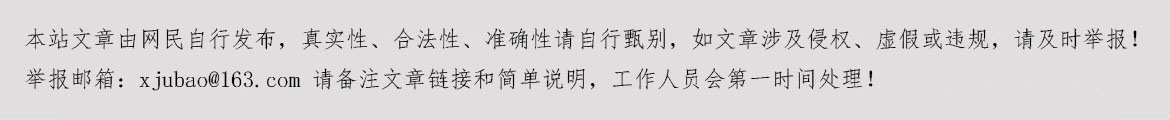
|
|
1
 鲜花 |
1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业界动态|佰企网

2025-04-28

2025-04-28

2025-04-28

2025-04-28

2025-04-28

请发表评论